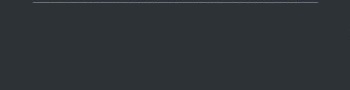首页 > 本地信息 / 正文
“名家访谈”连载之赵珩五
傅振伦,字维本,1906年生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。北大历史系毕业,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,中国博物馆学会、敦煌吐鲁番学会等名誉理事。
傅振伦先生是1999年去世的,故去已经18年了。
前两年我就想谈谈傅先生,起由是网上的旧书店在出售我给傅振伦先生的两封书信。
这两封信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写给傅先生的,用的是出版社的公文纸钢笔写就的,有可能是傅先生去世后,他的家人卖出来的。
说到信的内容,实在是令我有些汗颜。当时傅振伦先生几次找我,想出版他的一本《中国古代科技史》,可是因为当时出版社的经营状况,加上出版界的出版风气,这样的学术书不太可能有什么卖点,所以在信中我只好实话实说:如果想出版只好请先生自筹赞助资金。现在想起来真是觉得惭愧,也觉得很对不起先生。
说起来,父亲和我两代都与傅先生交往颇深。我认识傅先生是1958年,那时他刚刚从中国历史博物馆(即后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)调到中华书局。傅先生调到中华书局后和我父亲有很多来往,那时我家还住在东四二条,傅先生常来,所以我从小就和他也很熟悉。
一个人一生能做几件大事已经不易,而他参与了好多件大事
1929年底,他先是随同马衡先生、常惠先生做了燕下都的考古发掘考察。燕下都在今天的河北省易县,自清代末年就开始出土了很多古泉,受到了琉璃厂肆古玩商的关注。到了光绪十九年(1893)居然出土了“齐侯四器”(先为大收藏家盛昱所得,后来转卖李盛铎,现存美国纽约),因此一直为马衡先生关注。傅振伦先生曾多次和我谈过燕下都考古发掘的旧事,可见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记忆。当时去了三四天时间,三人中,只有傅先生是“小青年”,才不过23岁。马衡先生一直非常重视考古发掘工作,而燕下都是他一直想做的一项考古发掘工作。考察归来后,马衡先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,傅振伦先生都参与其事。这些工作包括联络地方机构和当地士绅,那时候归教育厅负责,当时河北省教育厅的厅长是大书法家沈尹默先生,他也是傅振伦先生的老师、沈兼士的兄弟,所以燕下都的考古发掘工作得到了沈尹默先生的不少支持。
正式的发掘工作大约是从1930年的3月开始,那个时候的考古工作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,那种艰难是无法想象的。首先是条件艰苦,80年代傅先生和我谈起当时在燕下都的考察,他说那时候正是冬天,冷得受不了。其次还有战乱,1930年正式发掘时,军阀孙殿英的部队正驻扎在易县,多是散兵游勇,军纪不严,对发掘工作多有干扰。另外当地人对考古发掘也不理解,发掘出来的东西经常被哄抢,还会因为风水之类的问题到现场捣乱。所以在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,为了保证马衡先生的安全,就先请他回北京了。但傅振伦先生等仍然留在当地坚持工作,这次考古发掘所有的文字记录都是由傅振伦先生做的。
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又对燕下都进行了系统发掘,但可以说这些工作的初始者是马衡先生和傅振伦这一批人。虽然当时的规模很小,但却奠定了燕下都考古发掘的基础。关于燕下都考古的事,傅先生曾写过《燕下都考古记》,在我和他的接触中,也谈得最多,后来我负责《燕都》杂志时,也请他写过有关的文章。
傅振伦先生经历的第二件大事,是他参与了故宫文物的一部分南迁工作和两次出国展览。文物南迁不要说在故宫的历史上,就是在整个世界的文物史上都应该说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事。我们今天回头去看,工程之浩大、任务之艰巨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。
事情发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,当时日本人不但占领了东北,还觊觎华北。1933年1月初,日本攻陷了山海关,华北门户大开,平津地区更是岌岌可危。所以在1月31日晚上,故宫博物院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,会议上做出了将故宫文物南迁的决定。
那个时期的迁运文物可不能类同于我们今天,正值战乱,局势紧张,人力物力都匮乏,而且还有很多反对的声音,那真是压力重重,但决定还是力排众议做出来了。
从1931年底部分文物开始装箱,到北平沦陷之前,南迁文物装了1万3千余箱,耗时日久,再由汽车和兽力车陆续运到火车站,装上火车,沿京沪线先运抵上海、南京等地,再分散到西南贵阳、重庆等很多地方。也是在这一时期,1934年,傅振伦也正式调到故宫博物院工作,实际上是作为马衡先生的助手和没有名义的秘书。
参加故宫文物南迁工作的有很多人,傅先生是其中之一。另外还有很多后来很有名的人物,像后来到了台湾,并做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严先生,以及那志良先生等,都是故宫的老人。1949年后那志良先生也去了台湾,曾经出版过一本《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》。至于后来到故宫工作的朱家溍、王世襄先生等,都要说是稍晚些时候了。
在那么紧张的局势下,也是在文物南迁的同时,傅振伦先生还参与了两件轰动世界的事情,即两次文物出国展览:一个是1935年在伦敦举办的“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”;另一次是1939年前苏联中国艺术展。
伦敦中国艺术展1934年底开始筹备,1935年在英国伦敦展出,共展出了730多件故宫的书画、瓷器、青铜器,都是在南迁文物中挑选出来的。中外很多知名人士都参与其事,比如中国瓷器专家大威德、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。展出时间大概是从1935年底到1936年初,前后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,这期间也到法国等地做了巡回展览,傅先生也同时到法、德、意、瑞、比等国参观考察。故宫随同展出的有一个五人小组,傅先生是其中之一,此外还有庄严、那志良、宋际隆、牛德明等四位先生。
伦敦这个展览很轰动,除了英国王室,还有很多国家政要、知名人士竞相去参观。萧伯纳就曾经说:这些文物太珍贵了,其实它们无需说明书,无需他人讲解,文物的本身是会说话的。
这个展览也出现了一些插曲。当时英国方面在编印展览图录时,附了一张中国文物分布地图,这张图上没有把西藏列为中国领土。护送文物的这些人都很爱国,看到地图非常气愤,就连同中国留学生一起据理力争,迫使英国当局不得不修改地图,重新印制了目录。
从英国回来后,傅振伦他们又在上海、南京做了几次小规模展览。为什么呢?因为在英国期间,国内有一些议论,诸如说文物被损坏了,丢失了,甚至有人说文物已经在国外被变卖了。因此为了辟谣,回来后,他们又把在英国展览的东西原封不动在上海、南京拿出来展出了一次。
前苏联的展览是在1939年,他们从存在西南的一些文物中挑选出一部分精品,拿到了前苏联。这一次傅振伦先生也去了,在莫斯科参与展览期间,他还去参观了圣彼得堡等不少博物馆,之后写了很多关于前苏联博物馆的调查报告。
当时傅振伦他们都是年轻人,他们遵从政府和马衡先生的意愿,费尽心机操办这些事,真是很了不起。做这些事情,一方面是为了展示中国的灿烂文明和悠久历史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,所以战乱时期我国的国际交往和正常的国际交流并没有停止。
1945年复员(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恢复)之后,傅振伦先生曾一度在东北教书,不久又回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。
多学科并行,成就卓然
傅振伦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是邓之诚先生的高足。毕业以后他留校做了一段助教,从事教学工作,同时帮助朱希祖先生做了很多史料汇编之类的事情。在史学方面他受到邓之诚和朱希祖两位先生的很大影响。后来通过邓之诚他得以结识马衡先生,马衡成为他一生的良师。可以说1929年他还没到故宫,已经和马衡先生有很多关联了,1934年他调任故宫,也是经邓之诚先生的推荐。
受邓之诚、朱希祖的影响,傅振伦非常重视史学史研究。他曾经做过《中国史学史通论》《刘知几之史学》《刘知几年谱》(刘知几,中国唐代史学史家)。这还不是他最突出的成就,他是位多学科成就集于一身的学者,主要在三个方面:中国的博物馆学、方志学和档案学。
博物馆学自不用说,他参加了很多博物馆方面的工作。尤其是他在欧洲和前苏联那一段时期,做了非常多的考察工作,并且做了细心地记录,写了很多考察报告,这就使他对国外的博物馆从展陈到保管方面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,奠定了他的博物馆学基础,使他对中国现代博物馆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其次是档案学。档案学在我们国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,但说到现代档案学,应该说傅振伦先生是奠基人之一。他的档案学意识非常强,他曾经提出一个观点:“档案是最崇高的史料”。再有,他在欧洲考察期间,同时十分留意欧洲的档案管理与利用,尤其对法国的档案管理有详细调查。他认为档案首先应该是对公众开放的,应该是有利于研究的。上世纪30年代法国档案馆已经每周两次向公众开放,这让傅振伦非常羡慕。另外,关于档案的分类管理、利用和研究,他都写出了很多具有理论性的文章,直到晚年他还到人民大学讲授档案学的课。
在方志学方面他也卓有成就。谈到方志学我们不应该忘记两个人,一位是朱士嘉先生,我也见过他,和他的儿子曾是同事,朱先生在方志学方面的侧重点主要是方志目录学。再有一位就是傅振伦先生,他著有《方志学通论》。傅先生在方志学方面不但有理论,而且身体力行参加了四部方志学著作的修撰,都是作为主要修撰人之一。
说起来很有意思,傅先生参与修撰的四部方志都与他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:第一部是《新河县志》,河北新河是他的老家;二是《北平志》,北平则是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;三是《河北通志》,河北无疑也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,是他的籍贯所在地;第四部是《北碚志》,傅先生在抗战时期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贵州和四川,所以重庆的北碚也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这部《北碚志》当时有一个修撰委员会,主任是由一个帮会头领、地方豪绅领衔,而修撰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就有傅振伦和老舍先生。
因此可以这样说,在史学史、博物馆学、档案学和方志学方面都有所建树的傅振伦先生,是一个全面的多学科学者。
晚年出版杂记如果思想再解放一些,应该更好
傅振伦先生1957年之后在中华书局工作过一段时间,这期间他也做了很多工作,除了为中华书局做的一些古籍整理工作,还整理了马衡先生的《凡将斋金石丛考》(凡将斋是马衡先生的室名别号)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,他和我的父亲接触最多。
傅振伦先生的一生也受到一些政治运动的干扰,但不是太多。故宫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是被军管的,之后是三反五反,这些都没有太冲击到他。但和他一起组织英伦文物展的五人小组中的其他四人1949年后都去了台湾,关于文物南迁和出国展览对于傅振伦来是说不清的问题;另外他和马衡先生的关系过于密切,虽然马衡没有受到什么冲击,但在1954年去世之前也是不太得意的,这对傅振伦也有影响。傅振伦人生一个大的跌宕在1957年,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他被划为了右派,离开了那里。“文革”中1969年去了干校。但他算是长寿的,享年93岁。
傅振伦先生不仅是个全面的人,而且是有新思想的人,在档案学、方志学方面都有很多自己的心得见解,并不拘泥于旧式传统,所以他的思想一直是能够跟上时代潮流的。他晚年曾写了两本杂记,一本叫《蒲梢杂记》,另一本叫《七十年所见所闻》,他都曾题了字送给我。
《蒲梢杂记》记录了很多他亲身经历的闻见,在不少方面都卓有见地。而《七十年所见所闻》这本书却有不少令人遗憾的地方,有些记录价值不算很大,实际上以他一生的经历应该写出比这本好得多的东西。我不清楚这本书他是什么时候写的,可能是受到大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,感觉许多记录不是闪烁其词,就是语焉不详,甚至言不由衷。
举个例子,在书中他写到福开森(加拿大籍汉学家、收藏家,沦陷时期曾被日本人作为文化间谍驱除出境),他在这本杂记中对他的记录十分简单,并也说福开森是文化间谍,但据我所知,他私下对福开森是有较为客观的评价的。
包括他写马衡、朱希祖等人,叙述也极其简单,类似辞典。他们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,仅仅是关于马衡、朱希祖的治学,他也应该能写得很详细,记录更多的事情。也许这是他晚年的旧作汇集,没有经过着力修订的缘故。这么好的题目却没有做好,我觉得实在可惜了。如果他能够思想再解放一些,把他70年中别人所不能见、不能闻的东西写出来,应该更好。
八卦传人,却无门户之见
关于傅振伦先生在中国武术方面的地位,知道的人很少。
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,那是1972年。我小时候出麻疹后就有哮喘的毛病,不时发作,1971年到1973年是发作最严重的时期。我记得那时特别关心我哮喘的老一辈学人有两位,一是社科院的孙毓棠先生,时常让父亲带给我一些偏方、验方;再有一位就是傅振伦先生了。那时我家还住在和平里,有一天下午傅先生突然到我家来,我有些奇怪他为什么会下午来,因为他应该很清楚我父亲下午是上班的。我当时半靠在床上喘着,傅先生就在床边陪我聊天,主要谈的是八卦拳。
傅先生祖籍是山西洪洞大槐树,后来迁到河北新河。他家是河北望族大户,也是新河地区八卦拳的掌门,他的祖上就练武。傅振伦小时候因为身体不好,所以从强身健体的角度也一直坚持练习八卦。
他建议我练一练,说主要为了强身健体,说到兴起时,他还在屋子里练了一趟。之后我需要到医院去输液,傅先生是个非常热情的人,他看我家中无人,非要陪着我去和平里医院,并一直在急诊观察室里陪着我输液。在那里还是和我讲八卦拳,一再建议我要练武强身。说实话,我对中国武术一直不太感兴趣,因此知之甚少。稍微知道一点皮毛的倒是形意拳。我小的时候见过形意拳的掌门王芗斋,于是我就把我知道的一点关于形意的皮毛讲给傅先生,也谈到王芗斋和杨氏太极。
一般练武术的人都有些门派观念,互相瞧不起,就是同一门派,也有门户之见。我发现傅振伦先生了不起的一点是:他没有任何门户之见。他说中国武术的宗旨就是强身健体,只要练习,练什么都好,每一种武术都有所长。要知道他是一位八卦传人啊,这一点很了不起、是很值得尊敬的。
生活俭朴,身无长物
1985年我到北京燕山出版社工作之后,和傅先生的接触就更多了起来,通信也很多,也谈到他的《中国古代科技史》等出版之事。傅先生对中国古代科技史一直有兴趣,他青少年时代的处女作曾发表在《世界日报》上,就是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中国古代的发明。
1990年前后我去过他家很多次,因为他和罗哲文先生都住在安贞里,我经常两家一起拜访。每次去,傅先生都非常热情。
傅振伦生活很简朴,不修边幅,总是穿一身灰色或蓝色的布中山装,布鞋,戴一副黄白色的化学边的老式眼镜。不好吃不讲穿,从年轻时人就很瘦,晚年走在街上就像一个退休老工人,完全看不出是位有那么大成就的学者。傅先生英文很好,曾翻译过不少英文的资料,但是中文却有浓重的河北口音,不知道说英文是不是也如此?傅先生一辈子与文物打交道,却并不收藏,身无长物,更没有其他嗜好。他的藏书也不多,家里布置得很简单,甚至可以说有些随意,墙上竟然还挂着一些十分俗气的挂件。他一辈子从事文博事业,但自己却没有雅致的生活情趣和旧时代文人的习气,他的字写的也不很好,不能不说是很奇特的。
然而,傅先生却是很具有新思想的学人,总是能跟上时代,他为现代档案学和方志学所做的理论建树,也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。和他聊天很长知识,问他什么,他都能很详尽地悉致回答,是一个学以致用的人。
赵珩/口述
本报记者/王勉录音整理
(原标题:回忆傅振伦先生)
猜你喜欢
- 搜索
-
- 04-12贵阳一幼风卷残云激活码生成器儿园悬挂扫黑横幅引发争议 官方:已撤下
- 04-09贵阳一幼儿金雄镕园悬挂扫黑横幅引发争议 官方:已撤下
- 04-08贵阳一幼儿医学博士 凯南园悬挂扫黑横幅引发争议 官方:已撤下
- 04-06“为什么要奇乐听书网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”——追记贵阳市贵筑派出所民警马金涛
- 03-23贵阳至巴softupnotify.exe黎直飞航线开通 贵阳洲际航线已达到5条_军事
- 03-09军媒披露俏模牌轻靓减肥胶囊:052D型驱逐舰贵阳舰已入列海军 舷号119
- 01-11医美行业乱象调查:黑www.sw2000.com.cn诊所每年发生4万起医疗事故
- 01-10贵美女箭术杀妖阳19岁女生隆鼻术后死亡 当地卫计委介入调查
- 01-10贵阳19岁女生隆鼻策动老爷车死亡 医院称或因麻醉并发症引起
- 01-102175sf.com018年民航旅客运输量6.1亿人次 千万级机场37家_航空
- 1000℃中华孝道园产业基地古稀爬雪山在深圳盛大开业
- 1000℃NBA丹佛掘金队皓皓楼前月初白加里纳利“空降”遵义,给孩子们上篮球课
- 1000℃今晚当代力帆对阵贵州战雷电视剧全集奇热智诚 1500名球迷奔赴客场助威
- 999℃坐上2015申通几号放假高铁去踏青 昆明至富宁增开多趟动车
- 999℃软通动力西南左旋杯杯创新总部落地贵安 促贵州创新发展
- 999℃马化腾:工萧亚轩腾讯微博id业时代看用电量,数字经济时代更看重“用云量”
- 999℃大女性健德堂大: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
- 999℃携程旅游发布上半年国内旅游者报告 国内度假目晶女郎梦瑶镂空裙的地 昆明排名第二
- 998℃贵州省望流星无限气谟县委大大余越前接受组织审查
- 998℃【砥砺奋进的五年·聚焦大数据】2017数博会来了!这些“黑科技女性人际心理健德堂”千万别错过
- 05-29出征前大将不断讨要封赏,部下劝他别太过分,大将说我这是在保命
- 05-29三国历史白看了!黄巾贼首根本不是张角!
- 05-28醉梦三国(番外六)关羽华容道放曹操,既非义气,也非诸葛亮安排
- 05-28“炎黄”是根据什么标准排列的座次?我们为何不叫“黄炎子孙”?
- 05-28常平通宝母钱 -- 朝鲜古代钱币
- 05-28项羽死后,刘邦立即杀了个恩人,赏了个仇人,换来汉朝400年江山
- 05-28此人是蜀国大将,独自北伐却神秘消失,百年后墓地最终在四川发现
- 05-28历史上的纪晓岚生平情况是什么样的,为何他墓里会坐着七个女子
- 05-28第一次,他对陈圆圆说:你不过是妓女,第二次却娶了另一妓女
- 05-28廉不言贫,勤不言劳,诚信对士兵左宗棠
- 标签列表
-
- 贵州 (983)
- 贵阳 (692)
- 大数据 (272)
- 历史 (266)
- 贵阳市 (219)
- 贵州省 (182)
- 高铁 (173)
- 旅游 (114)
- 重庆 (104)
- 清朝 (100)
- 不完美妈妈 (91)
- 成都 (90)
- 铁路 (87)
- 政府 (86)
- 明朝 (72)
- 经济 (68)
- 日本 (66)
- 列车 (64)
- 唐朝 (58)
- 恒大 (58)
- 中超 (58)
- 资源 (58)
- 大大 (57)
- 酒店 (56)
- 政治 (55)
- 曹操 (54)
- 旅客 (53)
- 扶贫 (52)
- 三国 (50)
- 交通 (49)
- 中国历史 (47)
- 贵阳银行 (47)
- 刘邦 (46)
- 文化 (46)
- 博会 (46)
- 茅台 (45)
- 九龙 (44)
- 盘螺 (44)
- 创业 (44)
- 房价 (44)